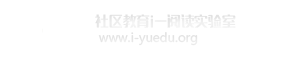-
画句子星期一
像写散文那样去画画
我是把一幅画当作一篇散文来写的,或者把一篇散文当作一幅画来画的。
画家如何一头准确地扎入颜色而不是酱缸里,这靠选择的角度。我的绘画基...星期一
像写散文那样去画画
我是把一幅画当作一篇散文来写的,或者把一篇散文当作一幅画来画的。
画家如何一头准确地扎入颜色而不是酱缸里,这靠选择的角度。我的绘画基本功差,表演纸上功夫会大显拙劣,所以看官不能以严格的绘画技巧来要求,那样有点抬举了我腕底一管狼毫,结果只能南辕北辙。你必须以文字水平标准来衡量颜色,以草茎来测量河流,看一幅图画是否表达出诗词的平仄。
意境大于笔墨技巧一直是我的纸做的挡箭牌。有这样一方玄虚的挡箭牌,我就可以随意添加语言,增删口水,羊角上挂满成语,随意加宽蟋蟀的道路和雪山头顶上的朱砂。
看色如读字。
我是一个可以把王维折叠起来行走的人,怀揣苏东坡像揣一个烧饼壮胆的人,那一刻,让你在纸上听到风声雨声咳嗽声叹息声。
2008年11月 -
秦岭记中国多山,昆仑为山祖,寄居着天上之神。玉皇、王母、太上、祝融、风姨、雷伯以及百兽精怪,万花仙子,诸神充满了,每到春夏秋冬的初日,都要到海里去沐浴。时海动七天。经过的路为大地之脊,那就是秦岭。
秦岭里有一条倒流河。河都是由...中国多山,昆仑为山祖,寄居着天上之神。玉皇、王母、太上、祝融、风姨、雷伯以及百兽精怪,万花仙子,诸神充满了,每到春夏秋冬的初日,都要到海里去沐浴。时海动七天。经过的路为大地之脊,那就是秦岭。
秦岭里有一条倒流河。河都是由西往东流,倒流河却是从竺岳发源,逆向朝西,至白乌山下转折入银花河再往东去。山为空间,水为时间。倒流河昼夜逝着,水量并不大,天气晴朗时,河逐沟而流,沟里多石,多坎,水触及泛白,绽放如牡丹或滚雪。若是风雨阴暗,最容易暴发洪涝,那却是惊涛拍岸,沿途地毁屋塌,群峦众壑之间大水走泥,被称之过山河。
白乌山是一块整石形成,山上生长两种树,一种是楷树,一种是模树。树间有一小庙。庙里的宽性和尚每年都逆河上行到竺岳。参天者多独木,称岳者无双峰。这和尚一直向往着能再建一个小庙在竺岳之巅,但二十年里并未筹得一砖一椽。只是竺岳东崖上有窟,每次他来,窟里就出水,水在崖下聚成了池子才止。窟很深,两边的壁上有水侵蚀的虫纹,排列有序,如同文字,又不是文字。和尚要在窟里闭关四十九天。
倒流河沿岸是有着村庄,每个村庄七八户人家,村庄与村庄相距也就二三十里。但其中有一个人口众多的镇子,字面上是夜镇,镇上人都姓夜,姓夜不宜发“爷”音,所以叫黑。黑镇是和尚经过时要歇几天的地方,多在那里化缘。
逆河上行,旱期里都沿着河滩,河水拐道或逢着山湾,可以从河中的列石上来回,一会儿在河南,一会儿在河北。河里涨了水,只能去崖畔寻路,崖畔上满是开了花的荆棘丛,常会遇到豺狼,褐色的蛇,还有鬼在什么地方哭。最艰难的是走七里峡,峡谷里一尽烟灰色,树是黑的,树上的藤萝苔藓也是黑的。而时不时见到水晶兰,这种“冥花”如幽灵一般,通体雪白透亮,一遇到人,立即萎缩,迅速化一摊水消失。饭时没有赶到村庄就得挨饿,去采拳芽,摘五倍子,挖老鸹蒜,老鸹蒜吃了头晕,嘴里有白沫。每次跟随着和尚的有十多人,行至途中,大多身上衣衫被荆棘牵挂,褴褛败絮,又食不果腹,胃疼作酸,或怕狼骇鬼,便陆续离开,总是剩下一个叫黑顺的。
黑顺是夜镇人,性格顽拗,自跟着郎中的爹学得一些接骨术后就不再听话,爹让他往东他偏往西,爹说那就往西,他却又往东。爹死时知道他逆反,说:我死了你把我埋在河滩。黑顺想,十多年不听爹的话,最后一次就顺从爹吧,把爹真的埋在了河滩。一场洪涝,爹的坟被冲没了。他幡然醒悟,在河滩啼哭的时候,遇见了和尚,从此厮跟了和尚。
两人逆行,曾多少次,路上有背袝荷担顺河而下的人,都是嫌上游苦寒,要往山下安家。顺沟逃窜的还有野猪、羚牛、獐子、岩羊和狐子。唯有一队黄蚁始终在他们前面,逶迤四五丈长,如一根长绳。到了竺岳,岳上树木尽半人高,倔枝扭节,如是盆景,在风中发响铜音。东崖的窟里出水,崖下形成了一池,一只白嘴红尾鸟往复在池面上,将飘落的树叶一一衔走。黑顺问:这是什么鸟?和尚说:净水雉。黑顺说了一句:今黑里做梦,我也做净水雉。和尚却看着放在脚旁的藤杖,觉得是条蛇,定睛再看,藤杖还是藤杖。
和尚到窟里闭关了,四十九天里不再吃喝,也不出来。黑顺除了剜野菜、采蘑菇,生火烧毛栗子,大部分时间就守在窟外。
一日黄昏,黑顺采了蕨根归来,窟口的草丛中卧着一只花斑豹。有佛就有魔。他大声叫喊,用木棒击打石头。花斑豹看着他,并没有动,鼻脸上趴满了苍蝇和蚊虫,过了一会儿,站起来,就走了。所有寺庙大门的两侧都塑有护法的天王,那花斑豹不是魔,是保卫窟洞的。黑顺一时迷糊,弄不清了花斑豹是自己还是自己就是了花斑豹。就坐在窟外捏瓷瓶。瓷瓶是打碎了装在一只口袋的稻皮子里,他手伸在稻皮子里拼接瓷片,然后捧出一个拼接完整的瓷瓶。这是爹教给他接骨的技术训练,他再一次把拼接好的瓷瓶捣碎,搅在稻皮子里,又双手在稻皮子里拼接。
黑顺的接骨术已经是很精妙了,跟和尚再往竺岳,所经村庄,只瞅视人的胳膊腿。凡是跌打损伤,行动不便的,就主动诊治,声明不收分文,能供他师徒吃一顿饭或住一宿就是。和尚在给人家讲经的时候,他坐在柴棚里喝酒,得意起来,失声大笑,酒从口鼻里都喷出来。 -
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后来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,就像是一杯水,在这样的一杯水里放上一把盐,结果显而易见,这杯水咸到无法下咽。但如果你把这把盐撒到湖中,湖水不会有什么改变,你甚至感觉不到咸味了;如果这把盐撒到海里,那它们只是融为一体。我就如同那杯水,对痛苦和缺憾特别敏感,总...后来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,就像是一杯水,在这样的一杯水里放上一把盐,结果显而易见,这杯水咸到无法下咽。但如果你把这把盐撒到湖中,湖水不会有什么改变,你甚至感觉不到咸味了;如果这把盐撒到海里,那它们只是融为一体。我就如同那杯水,对痛苦和缺憾特别敏感,总是感到生活咸得无法下咽,但这只是因为太狭窄,容量太小。生活中总会有一把盐撒下来,生老病死、聚散得失是每个人的必然风景,是生命的常识。所以问题所在,只在于我们是怎样一种容器,是一个杯子,还是一个桶,一个缸,我希望至少成为一个湖,最终成为大海。
▶
戏受到喜爱,我其实是受宠若惊的,这并不理所当然。年轻时,对周围人总有点隔膜,这些作品并不是为其他人所写的,只是自己纠结的脑袋里蔓延出的藤蔓。你被某种东西充满,表达是自然的流露。你写,并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,但是别人给了你美好的回馈,从《恋爱的犀牛》开始演出,我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时候,开始都有点不相信,然后就是非常感激。你一个人在说悄悄话,旁边不经意走过的人听见了,给了你很大的鼓励和安慰,说到《恋爱的犀牛》的时候,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▶
从今天起和世界握手言和。握手言和是接纳,有接纳,才有广阔和自由。做一个杯子肯定是不自由的,因为它有限制,它被空间隔断得很小。我在寻找更大的自由。
▶
戏剧确实是一个心理的空间,它制造了一种氛围,它能让你说出你平时说不出的话,你内心的呐喊或暗语。戏剧就是这样一个空间,它针对我们的心灵,而不是日常生活。
▶
一直说自己是诚实的作者,不曾言不由衷,生命中遭遇的种种自我蜕变、各种印迹都袒露在作品里、舞台上。“与生命握手言和”,是现在我想对大家说的话,也是这十几年来写的“悲观主义三部曲”最后想说的话。
▶
所有打过来的浪头,都会帮助你。真是这样。只有经历过这些以后,人才能不那么狭隘。没有经历过困惑和痛苦的人,一般都会较为肤浅。应该感谢生活给你的礼物,然后照单全收。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动力,毋庸置疑。生活总要继续下去。
▶
原来一直试图寻找完美的人,只对优秀的人感兴趣,希望看到优秀的人,让我对人类抱有希望。我自己不是天才,但我确实喜欢天才,有一阵子热衷于跟我认为的天才泡在一块儿,感受他们与世界和自我的互动,他们对生命采取什么态度,用什么方法应对这个世界,最终他们发现了什么,是否满足?这些对我特别有吸引力。通过这些优秀的人,我辨识道路,知道自己应该去向何处,我探究每一条路的出口何在,每一处山顶的风景如何。我想看到人的极限能到什么样子,看到他们能创作出什么稀奇之物。通过他们,我不必再费尽心力爬到塔尖,我看到只要是人,总有他的困惑,他的痛苦,他的问题,他的局限。现在我对每个普通人都感兴趣。 -
暗光列车
隧道刚刚诞生几分钟。墙壁还冒着汽,有的地方甚至还隐隐发亮,好像由什么酷热的东西挖掘出来的。地面上一双铁轨向大山的心脏飞驰,延伸近一公里,之后隧道在一块空荡荡的岩壁前戛然而止。四壁和天花板熔...
隧道刚刚诞生几分钟。墙壁还冒着汽,有的地方甚至还隐隐发亮,好像由什么酷热的东西挖掘出来的。地面上一双铁轨向大山的心脏飞驰,延伸近一公里,之后隧道在一块空荡荡的岩壁前戛然而止。四壁和天花板熔化出一道拱门:它的材料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骨头,但其实什么也不像。
拱门开始隐隐发光。这光没有颜色,似乎也没有光源。这光像飘拂飞扬的窗帘,充满整个拱门。一阵轻风穿过,混杂着隧道那还温热的墙壁上烤焦的花岗岩味道,带来海的气息。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吸。
突然,一辆火车凭空而出。一个红色的老火车头拖着三节车厢,不可思议地从那光帘背后冲出来。未见火车先闻其声,火车的歌声和引擎的响声先行一步在隧道里响起。第一节车厢里有两名乘客把脸紧紧贴在窗上:一个精瘦的棕发男孩,名叫岑·斯塔灵。一个女孩,名叫诺娃。其实她根本不是女孩。
起初他们只看见隧道壁上那烧焦的平滑岩石向后退去。接着他们从隧道口里冲出来;墙壁不见了,火车奔驰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。海市蜃楼般的景色闪过,火车两边都有奇怪的锤头样的东西立起,连诺娃都觉得可怕,还好她后来意识到那只是些岩石。一片片宽阔的潟湖像摔碎的镜子,反射出灰蒙蒙的蓝天、几轮太阳和许多白天也在闪闪发亮的星星。
岑和诺娃不是第一次乘火车从一个世界旅行到另一个世界了。他们来自星罗帝国,那里车站遍布半个星系,由凯门连接,火车只消一次心跳的工夫就从一个行星驶入另一个。但他们刚刚穿过的这个凯门是新的:这个凯门原来根本不应该存在,而他们懵懂地穿过,驶向未知。
“一个新世界,”诺娃说,“新的太阳照耀下的新行星。这个地方除了我们,从没有人见过……”
“可这里什么都没有!”岑说,有点失望,又有点释然。他不确定自己期待什么。神秘的城市?发光的高塔?上百万个车站天使起舞欢迎?这里只有潟湖、低矮的草丛,还有发红的岩石,时不时还有一丛像褪色的旗帜样的东西耸立在阴影中。
火车开腔了。红色的老火车头大马士革玫瑰有自己的思想,就像星罗帝国的所有火车一样。“大气是可呼吸的,”她说,“检测不到交流信号——我完全接收不到信号系统或是轨道交通控制系统的信息……”
诺娃是个机器人:一个人形的机器。她用自己的无线大脑扫描了这些波段,搜寻这个世界的数据海。什么都没搜到。只有静电的呼啸声,还有些一百万光年之外的一颗类星体的无意义的颤音。 -
火星编年史
一九九九年元月 火箭之夏
一分钟前,俄亥俄州还笼罩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之下。大门深锁,窗户紧闭,块块窗格也因霜雪的覆盖而失去了光彩;细长的冰柱如珠帘般自屋檐垂下;...一九九九年元月 火箭之夏
一分钟前,俄亥俄州还笼罩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之下。大门深锁,窗户紧闭,块块窗格也因霜雪的覆盖而失去了光彩;细长的冰柱如珠帘般自屋檐垂下;孩童在山坡上滑雪嬉戏;主妇们则在冰冻的街道上踽踽而行,身着厚重的衣物,像极了紧紧裹着毛皮的黑熊。
倏地,一股绵长的暖意穿过了这座小镇。热风如海水般恣意泛滥奔流,仿佛有人忘了将面包烘焙坊的大门关上。热浪惊动了小屋,唤醒了树丛,直往小孩身上招呼。冰柱坠落、粉碎,随即化为一摊清水。
门扉打开,窗户拉起,孩子们纷纷褪去毛织服饰,主妇也卸下她们熊一般的伪装。地上霜雪初融,现出昨夏青葱的草地。
火箭之夏。话语在开敞通风的房舍间口耳相传。火箭之夏。温暖、干燥的空气改变了窗上冰霜所构成的图案,拭去冬季特有的自然艺术。突然间,雪橇与滑雪板完全失去作用。雪,原本欲从寒冷天空下落至镇上的土壤,也在坠地之前就变成热呼呼的雨滴。
火箭之夏。人们倚靠在滴水湿漉的门廊,仰望着泛红的苍穹。
火箭矗立在发射场,大口大口地喷出粉红色的火光和热气。在这个寒冬的早晨,它却直挺挺地站在那儿,每一次深呼吸都带着夏日的信息。火箭,改变了时节;夏,就在短短的刹那,驻足于这片冰封的土地…… -
一花一世界:跟季羡林品味生活禅
一想到故乡,就想到一个老妇人。我自己也觉得奇怪:干皱的面纹,霜白的乱发,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,嘴瘪了进去。这样一张面孔,看了不是很该令人不适意的吗?为什么它总霸占住我的心呢?但是再...
一想到故乡,就想到一个老妇人。我自己也觉得奇怪:干皱的面纹,霜白的乱发,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,嘴瘪了进去。这样一张面孔,看了不是很该令人不适意的吗?为什么它总霸占住我的心呢?但是再一想到,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了这老妇人,便立刻知道,她不但现在霸占住我的心,而且要永远地霸占住了。
现在回忆起来,还恍如眼前的事。——去年的初秋,因为母亲的死,我在火车里闷了一天,在长途汽车里又颠荡了一天以后,又回到八年没曾回过的故乡去。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是什么时候,只记得才到故乡的时候,树丛里还残留着一点浮翠;当我离开的时候就只有淡远的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了。就在这浮翠里,我踏上印着自己童年游踪的土地。当我从远处看到自己的在烟云笼罩下的小村的时候,想到死去的母亲就躺在这烟云里的某一个角落里,我不能描写我的心情。像一团烈焰在心里烧着,又像严冬的厚冰积在心头。我迷惘地撞进了自己的家。在泪光里看着一切都在浮动。我更不能描写当我看到母亲的棺材时的心情。几次在梦里接受了母亲的微笑,现在微笑的人却已经睡在这木匣子里了。有谁有过同我一样的境遇的么?他大概知道我的心是怎样地绞痛了。我哭,我哭到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哭。渐渐地听到四周有嘈杂的人声围绕着我,似乎都在劝解我。都叫着我的乳名,自己听了,在冰冷的心里也似乎得到了点儿温热。又经过了许久,我才睁开眼。看到了许多以前熟悉现在都变了但也还能认得出来的面孔。除了自己家里的大娘婶子以外,我就看到了这个老妇人:干皱的面纹,霜白的乱发,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,嘴瘪了进去……
她就用这瘪了进去的嘴,一凹一凹地似乎对我说着什么话。我只听到絮絮的扯不断拉不断仿佛念咒似的低声,并没有听清她对我说的什么。等到阴影渐渐地从窗外爬进来,我从窗棂里看出去,小院里也织上了一层朦胧的暗色。我似乎比以前清楚了点儿。看到眼前仍然挤着许多人。在阴影里,每个人摆着一张阴暗苍白的面孔,却看不到这一凹一凹的嘴了。一打听,才知道,她就是同村的算起来比我长一辈的,应该叫做大娘之流的,我小时候也曾抱我玩过的一个老妇人。
以后,我过的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日子。母亲的死使我对一切都灰心。以前也曾自己吹起过幻影:怎样在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以后,回到故乡来,听到母亲的一声含有温热的呼唤,仿佛饮一杯甘露似的,给疲惫的心加一点儿生气,然后再冲到人世里去。现在这幻影终于证实了是个幻影,我现在是处在怎样一个环境里呢?——寂寞冷落的屋里,墙上满布着灰尘和蛛网。正中放着一个大而黑的木匣子。这匣子装走了我的母亲,也装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。屋外是一个用黄土堆成的墙围绕着的天井。墙上已经有了几处倾地的缺口,上面长着乱草。从缺口里看出去是另一片黄土的墙,黄土的屋顶,黄土的街道,接连着枣树林里的一片淡淡的还残留着点绿色的黄雾,枣林的上面是初秋阴沉的也有点黄色的长天。我的心也像这许多黄的东西一样地黄,也一样地阴沉。一个丢掉希望和幻影的人,不也正该丢掉生趣吗?
我的心,虽然像黄土一样地黄,却不能像黄土一样地安定。我被圈在这样一个小的天井里:天井的四周都栽满了树。榆树最多,也有桃树和梨树。每棵树上都有母亲亲自砍伐的痕迹。在给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,还有母亲没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,半棵葱。吃饭用的碗筷,随时用的手巾,都印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。在地上的每一块砖上,每一块土上,母亲在活着的时候每天不知道要踏过多少次。这活着,并不邈远,一点儿都不;只不过是十天前。十天算是怎样短的一个时间呢?然而不管怎样短,就在十天后的现在,我却只看到母亲躺在这黑匣子里。看不到,永远也看不到,母亲的身影再在榆树和桃树中间,在这砖上,在黄的墙,黄的枣林,黄的长天下游动了。 -
时间机器
时间旅行者(为了方便就这样叫他吧)在向我们解释一件深奥的事,他灰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,平日里苍白的脸也因激动而涨得通红。炉火烧得很旺,玻璃杯里不断冒出又消失的气泡,映出银制百合花灯罩里白炽灯...
时间旅行者(为了方便就这样叫他吧)在向我们解释一件深奥的事,他灰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,平日里苍白的脸也因激动而涨得通红。炉火烧得很旺,玻璃杯里不断冒出又消失的气泡,映出银制百合花灯罩里白炽灯射出的柔光。我们坐的椅子是他的专利,坐在上面,仿佛能感受到拥抱和爱抚。晚餐后氛围舒适,思绪任意驰骋,不受丝毫束缚,他就这样对我们述说着,用一根瘦削的食指滑过要点,而我们坐在那儿,懒洋洋地欣赏着他对这个新的谬论(我们是这么觉得的)的认真和创造。
“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讲。我必须反驳一两个几乎被公认为正确的观点。比如说,学校里教的几何就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。”
“要我们从这里开始理解,未免太颠覆了吧?”菲尔比说。他一头红发,喜欢与人争辩。
“我不是要你们接受什么无稽之谈,你们很快就会认可我要你们理解的一切。你们应该都知道,数学上所谓一条线,一条宽度为零的线,是不存在的。这你们学过吧?这两者其实都不存在,还有数学上所说的平面,这些纯粹只是抽象的东西。”
“没错。”心理学家说。
“只有长、宽、高的立方体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。”
“这我不同意。”菲尔比说,“立方体当然可能存在。所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都……”
“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想一想,瞬时立方体是否存在?”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菲尔比说。
“一个没有任何持续时间的立方体,真的存在吗?”
菲尔比陷入沉思。
“显然,”时间旅行者继续说道,“任何真实存在的物体都必须有四个方向的延伸:它必须有长度、宽度、高度和——持续时间。但由于人类的自然缺陷,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事实,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解释。实际上存在四个维度,其中三个我们称为空间的三个平面,第四个维度是时间。但是对我们而言,前三个维度和后一个维度之间有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区分线,因为我们的意识从生命开始到结束,都是沿着时间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地向前移动的。”
“这,”一个年轻男人说,他小心翼翼地就着烛火重新点燃雪茄,“这……非常清楚。”
“现在,这一点被太多人忽视了,这非常重要,”时间旅行者继续说,脸上带着一丝兴奋,“这就是所谓第四维度,虽然有些人嘴上说起四维,自己却不知道具体意思。这只是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式。时间和其他三个维度没有什么不同,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向前移动的。但有些笨蛋却搞错了,你们都听过他们是怎么说第四维度的吧?”
“我没听过。”市长说。
“很简单,数学家认为空间有三个维度,我们可以称之为长、宽、高,而且始终可以通过三个互成直角的平面来表现。但有一些哲人总在问为什么是三维——怎么没有另一个维度和其他三个维度互成直角呢?——甚至试图构建出一个四维几何。大约一个月前,西蒙·纽科姆教授还向纽约数学学会解释这个问题。你知道,我们可以在一个二维平面上表示三维立体图形,同样,他们觉得,只要能掌握透视法,就可以在三维模型上表现出四维。明白了吧?”
“我想是的。”市长喃喃地说。接着,他皱起眉头,陷入思考,嘴唇翕动着,像在重复着什么神秘话语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是的,这下我明白了。”神色豁然开朗。
“好,我可以告诉你们,我研究四维几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我的一些结论会让你们觉得奇怪。比如,这里有几幅男人的肖像,这幅是8岁,这幅是15岁,这幅是17岁,这幅是23岁,以此类推。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他的四维存在在三维中的体现,而他的四维存在是固定的、不可改变的。” -
假如我能使一颗心不破损那些感觉不到这爱的人
那些感觉不到这爱的人
要拉动他们就像拉动河流
那些无法畅饮黎明
犹如一杯春泉的人
... -
低入尘埃 菲利普·罗斯全集一、窘迫
他魅力顿失,激情枯竭。在舞台上他从来不曾失过手,他所作的一切都那么铿锵有力和成功,接着可怕的事情来了:他不能表演了。登台已成为痛苦不堪的折磨。他不再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创造奇迹,相反心里清楚会必败无疑。这种感觉...一、窘迫
他魅力顿失,激情枯竭。在舞台上他从来不曾失过手,他所作的一切都那么铿锵有力和成功,接着可怕的事情来了:他不能表演了。登台已成为痛苦不堪的折磨。他不再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创造奇迹,相反心里清楚会必败无疑。这种感觉接连出现了三次,最后一次出现时已经没有任何人感兴趣,没有任何人来看了。他已经招不来观众。他的才华消陨殆尽。
当然,如果你拥有这份才华,肯定也会有异于常人之处。我生来就跟常人不同,阿克斯勒对自己说,因为我就是我。那种特质跟我形影不离——这点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。可是,曾经环绕他的光环,以及所有那些做派、怪僻和个人特立独行之处,那些曾为出演福斯塔夫和培尔·金特以及万尼亚服务的气质——作为古典戏剧演员中最后的高人,那种给西蒙·阿克斯勒带来显赫声名的东西——如今没有一丁点儿可以给他的任何角色派上用场了。曾让阿克斯勒显得卓尔不群的一切,现在反而把他弄得像个疯子似的。他每时每刻都惦记着自己在舞台上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。过去,只要表演,他脑子里就什么杂念都没有。他表现得最出色的东西全都出自本能的发挥。现在他脑子里可谓无所不想,而且各种东西同时纷至沓来,生命力惨遭扼杀——他试图借助思考来控制它,到头来却消灭掉了它。认了吧,阿克斯勒告诉自己,看来他是碰上倒霉期了。虽然已经年过六十,没准这个霉头终会过去,因为他仍然承认自己还是不错的。何况他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倒霉期的经验老到的演员了。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。我以前就碰到过,他心想,所以我终究会找到解决的出路。这次我虽然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出路,但我定会找到——定会挺过去。
到头来还是没挺过去。他不能表演了。从前在舞台上专心致志的本事没了。现在每一场演出他都害怕,而且提心吊胆的感觉会长达一天之久。他经常花整天的时间思索这辈子在上场表演前从不思索的问题:我可能会失败,我演不好,我在扮演不当的角色,我的表演太过火,我的表演虚情假意,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第一句台词。其间,他巴不得干上一百件貌似不做不行的事儿来佯做准备以消磨时间:我得再看眼对白,我得休息,我得练习,我得再看眼对白,到该登台演出时,他早已精疲力竭。这时他又害怕上台了。听到提醒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迫近,他心想自己这回可能要演砸了。他等着快点开始,早点解脱好了,等着变成现实的刹那快点到来,等着忘记自己是谁,变成扮演这个角色的人,可是他却站在那儿,头脑完全茫然,做着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时才会做的那种动作。他既不能表现什么又无法收回去;他的表演既不流畅,也不内敛。表演成为一种夜复一夜、试图解脱某种东西的操练。